界面新闻记者 |
界面新闻编辑 | 黄月
文学就是讲,一个人一生多么地艰难,目标还没有求到,在半路已经失败的故事,这也就是《红楼梦》写的故事。
作家白先勇解读《红楼梦》,从中国人的生命历史开始讲起,他将人的一生,青年、中年、老年分别对应上儒家、道家与佛家:年轻的时候,大家都是入世哲学,儒家那一套,要求功名利禄;到了中年,大概受了挫折,于是道家来了;到了最后,要超脱人生境界的时候,佛家就来了。“中国人既出世又入世的态度,常常造成文化的一种紧张,也就是说,我们的人生态度在这之间常常有一种徘徊迟疑,我想,这就是文学的起因。”白先勇写道。
白先勇从《红楼梦》中读出了中国人的人生处境,也提醒读者注意《红楼梦》所代表的中国小说成就。西方文学伟大的作家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普鲁斯特,都善于长篇累牍地叙述分析,写得非常深刻,而中国小说大部分都是利用对话来推展情节,用对话来刻画人物。什么人讲什么话,语气口吻与内容都重要,而《红楼梦》他认为是对话写得最好的小说。
近年来,小说家白先勇致力于昆曲的复兴与《红楼梦》程乙本的重读与推广,先后出版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》《白先勇细说牡丹亭》。在他看来,对于传统小说、戏曲的推崇,是在救赎近现代中国人“情与美”的失落。
白先勇,生于1937年,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评论家、剧作家。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,美国爱荷华大学大学创作硕士。著有短篇集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《台北人》《纽约客》,长篇小说《孽子》,散文集《树犹如此》等,舞台剧剧本《游园惊梦》,电影剧本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《玉卿嫂》等。
八月中,在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推出二十年之际,界面文化与作家白先勇连线,听他讲述对于中国人“情与美”的理解,以及对现代年轻人情感的观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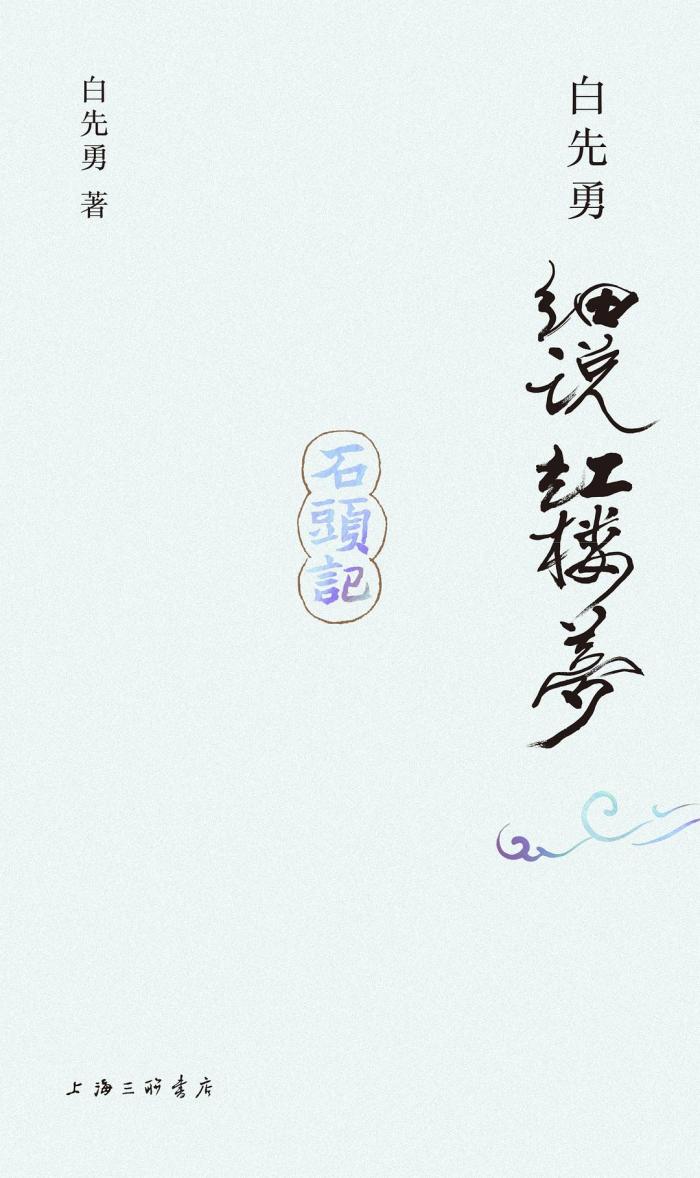
白先勇 著
理想国·上海三联书店 2024-2
01 现代文化断层后,中国人对情与美失去信心
界面文化:在《红楼梦幻》及《细说红楼梦》里,你分析《红楼梦》,是从中国的文化心理还有神话的角度入手的,可以讲讲原因吗?
白先勇:因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心理、文化的反射,不光中国,各国的神话都是如此。《红楼梦》从女娲补天开始写起,女娲是创造人类的、地母型的神,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上的开始。《红楼梦》整个神话架构是很庞大的。我们整个民族对情的关联很深。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神话,变成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三生情定。林黛玉下凡后要拿眼泪还债。爱情神话在我们的神话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
界面文化:之前谈到《牡丹亭》的时候,你提出现代的中国人有一种“情与美的失落”,失落是从何而来的?
白先勇:这个失落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很有关系。19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文化遭受了断层的危机,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很多,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。传统中国文化里情与美的因素很重要,断层以后,我们这个民族对中国的美学失去了信心,中国人的感情表露也手脚无措了。《牡丹亭》整部戏是爱情的神话,把情吊得最高,情真、情深、情至,情字最高,穿越生死——情是一种救赎的力量,所以我说昆曲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的感情,要把情与美两个因素流传下来。
我做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两岸三地很多地方,是从来没有见过昆曲的,那些大学生也反应激烈极了,那就是勾动了传统文化本来就有的情与美,勾动了文化基因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已经二十周年了。九月份我们在北大又要演出。之前在北大演过四次,那里讲堂很大,以前也都是满座。
界面文化:刚才讲到了北大,北大是“五四”的发生地,你在《红楼梦》序言中说,写这本书是有感于“五四”后的文科教育的衰落。
白先勇:没错,“五四”以来教育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都是如此,重理工、偏人文,现在更加厉害,因为大家了解到理工科容易找工作。但是人文的底子很要紧,如果没有人文做根基,很容易失去方向,AI来了也被牵着鼻子走。“五四”以来的教育的确是偏废,尤其是传统文化方面,中国传统绘画、山水花鸟这么了不起的传统,在学校里不重视,要学西洋画、画素描。昆曲这么丰富,两千多个曲牌,这样的音乐遗产,它的音乐性怎么没有被大量研究,都被排除在教育课程的外面了。(这样做)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伤害很大的。
现在的年轻学生对文化认同不完整,感到很茫然,就是因为教育偏废了传统文化。不是说不应该学西洋文化,西洋文化很伟大,可是要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,再去接受非常复杂的西方文化。现在很粗浅地去学习西方的绘画和音乐,这只是表面的,更深层、幽远的传统没法学,所以不如把自己的文化先扎根。
我在加州大学教书的时候,他们一年级的学生都要上一门通识课叫《西方文明》,教材是很厚很大的一本书,从希腊罗马一直讲下来的,这样大学生起码对西方的文明传统有基础的了解。我主张中国大学生也应该有一本完整的中华文明史,应该组织很多专家来编写这本教材。文明史的教育很重要,我们缺了这一课。
界面文化:按照“五四”很多学者的观点,恰恰是中国文字太难、文明太深,造成了文化阶层和大众阶层彼此不太沟通,没有那么容易普及?
白先勇:没错,那是“五四”时代说的,因为那时候要急功近利,救亡图存,中国处在很大的危机当中,要很快很短时间就要见效。现在讲起来中国文字难,学英文外语不是更难吗?中国戏曲很难,听外国的歌剧还不是一句不懂?意大利文哪里懂呢?还不是照样……我们觉得学文学很难,微积分、物理还是很难啊。难不能当成一个借口,大学教育就是要克服困难。汤显祖的那些诗很深的,美得不得了,我们在编的时候,只删不改,按原文唱的。那些年轻人半懂不懂,也被迷住了。
界面文化:说到音乐和绘画的失落,那么白话小说、明清小说传统在现代也失落了吗?
白先勇: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章回小说都一律排斥,说它们思想陈旧,“五四”以后外来翻译的(成为主流),我反而觉得翻译的语言不一定有很好的影响。翻译的文笔反而不顺、不通。其实像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还有晚清的《儿女英雄传》的白话已经非常纯粹了,这个传统不应该断掉、丢掉。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,可是我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,也尽量避免西化的句子。中文有自己的逻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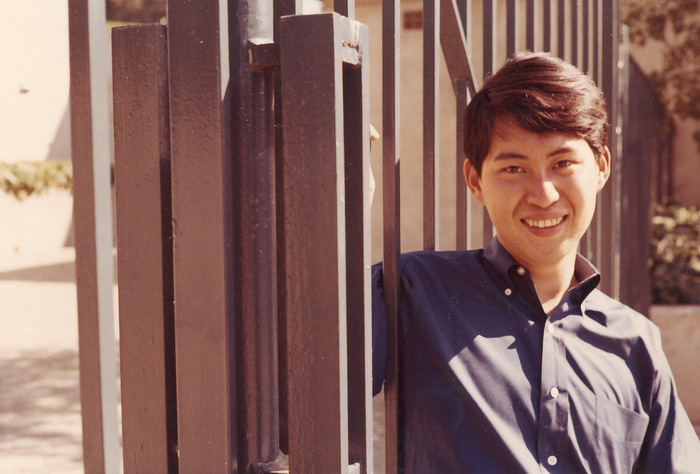
界面文化:回想当初在台大学习的时候,老师是怎么上文学课的?
白先勇:我们在台大虽然念外文系,常常去中文系听课,听叶嘉莹的诗选还有读诗,郑骞先生的词,王叔珉先生的《庄子》,有意无意,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融合起来。
02 青年人看起来对于爱情比较现实随便,实际上还是渴望天长地久
界面文化:讨论《红楼梦》或《牡丹亭》,都常常提到情。情有什么魔力吗?
白先勇:中国人对情这个字很重视,情几乎是宇宙的原动力。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,用英文翻译“情”还翻不出来。我们说“情根”,“情根一点,是无生债”,这是《牡丹亭》里的。好像情一旦生根,一生一世还不完的债。我们相信情对我们的巨大影响。
界面文化:情的中国文化内涵是什么呢?
白先勇:中国人的情不光是男女之情,对自然、对宇宙、对人伦,是无所不在的,是无限大的,所以英文很难传达。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比较理性的,美国也是,理重于情,英文不放纵情的。中国不管儒家道家佛家都有相当复杂的含义。中国人相信前世今生,前世欠的债,今世来还。动了情之后一辈子也还不完。人海茫茫,为什么对这个人特别动情呢?好像有的人一动情就是一辈子,有的人来来往往都不知道情根所在,这是很复杂的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演了五百多场,我跟着两百场,学校里头像是北大、北师大,那些学生对《牡丹亭》的反应热烈出于我的意料。
界面文化:从年轻人对《牡丹亭》的反应来看,现在年轻人是情深还是情浅呢?
白先勇:不能光看表面的,好像现在的青年人对于爱情比较现实随便,深一层看,每个人心底里面还是渴望天长地久理想的爱情。看《牡丹亭》那么感动,那相当于他们的梦嘛,做一个的爱情神话的梦。也许现实里这样的爱情轮不到他们,没那么容易。现在的年轻人跟古代也差不多,渴望相通的,表现的方式也许不一样。

界面文化:对于当代读者来讲,了解《红楼梦》这样的悲剧,有什么样的意义?
白先勇:读《红楼梦》很大意义上是了解人生的无常,兴衰无定,对世事的更加清楚。现在变化太快。科技日新又新,生命好像急流一样,要怎么抓住现在、怎么应付未来,对自己的处境要了解,才不会迷失。
03 两百多年来,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跟《红楼梦》并肩
界面文化:你认为《红楼梦》如同一部象征寓言,象征着中华文明的走向:因为发展到极致只能往下走的趋势,可以讲讲诗式的挽歌这样的写法吗?
白先勇:中华民族的文化到了18世纪乾隆时代已经到了极盛,只能往下走,其他的文化也是如此,所以才会产生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必须在乾隆时代产生,承接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,诗经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到明清的小说戏剧,哲学上儒释道三教在乾隆时代也成熟到顶点。艺术家可能有第六感的,非常敏感地,对于未来有一种敏感的觉醒,表面上曹雪芹写贾家的兴衰,或者说曹家的兴衰,在更大意义上,他感觉到中华的文明到了这个时候要衰落下去了,从这个意义上讲《红楼梦》是挽歌,而且是史诗规模的挽歌。
界面文化:在解读《红楼梦》时,你很细致地提到了很多种写法,譬如说非单线的、而是复杂多面的镜像式的写法,鬼魂作为预兆出现提示结局等等。看到这些写法,是出于自己的经验,还是出于和西方经典的对读?
白先勇:我自己写小说,所以看《红楼梦》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,为什么《红楼梦》写得那么好?那么动人?每个细节是怎么处理的?人物是怎样的?它每个细节的手法都是非常高妙的,整个结构就像明清时代大的传奇一样,由几百个折子戏一个个凑成,看起来好像琐琐碎碎,拼起来又是一出完整的大戏。它前面写的,后面一定用得上。从小说技巧看,高妙得不得了,用象征,用神话,也用现实,写实的部分写得太真实——大家总把它当做写实小说,写18世纪贵族小说林林总总,其实上面还有非常宏大的神话结构。象征和写实两方面合起来,构成了非常庞大深奥的一本书。
界面文化:从写作角度来讲,是写实更难,还是象征更难?
白先勇:两个都不容易,还要合得起来。书中超现实的部分,宝玉到太虚幻境,让读者以为真有这么回事,宝玉跟着警幻仙姑,一下子又回到红尘、现实生活里。一上一下,上天下地,来去自如。作者写实的本事非常厉害。
讲到底,文学小说就是文字艺术,《红楼梦》不仅集合了诗词歌赋还有戏曲,散文叙述也用得非常好。对话再巧妙不过了,小说的对话很要紧。大大小小人物那么多,每个人一开口就是他的个性,我说这是撒豆成兵,吹口气就有生命了。现代文学有科幻小说,也是超现实,《红楼梦》写神仙、太虚幻境,老早就是科幻了。写实主义来讲,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到它的地步。两百多年来,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跟它并肩。
界面文化:也有学者认为《金瓶梅》的成就也很高,并不比《红楼梦》弱。
白先勇:《金瓶梅》也高的。《金瓶梅》是晚明时代出现的,比《红楼梦》早两百多年。晚明时期兴起一种哲学,颂扬情的解放,还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。一方面出了《牡丹亭》,一方面出了《金瓶梅》,都是在书写人的感情跟人的肉体的大解放。
《金瓶梅》也是一部天才之作,能够把人的肉体和现实完全不避讳地写到顶,不过和《红楼梦》还是不能比的。《金瓶梅》被困扰在写实的、肉体的层面,《红楼梦》超出了这一层,有了精神上的超越。我觉得《红楼梦》要比《金瓶梅》高一头,不过《金瓶梅》对家庭生活的写实也很厉害。《红楼梦》在一些地方也受过它的影响,比如刻画人物,用穿着和饮食非常细微地写出来,也用诗歌穿插。这两部作品是一脉相承的。
04 完整的人格比功利的成就在某方面说更重要
界面文化:你曾提出所有中国人的生命都会经历儒释道的三个阶段,从开头的热心入世,到中年可能遭遇挫折,到老年的“空”和“无常”和“命运”,这样对生命历程的观察从何而来?
白先勇:一方面是观察而来,另一份方面是我自己的体会,我现在已经到了暮年了,看到周围的人……中国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儒家,求功名,拼命念书找工作。年轻人都是入世的、急进的、积极的。到了中年受了一些打击,有些丢官、坐牢,有些股票蚀本了,有些婚姻破裂了。这时候中国人另外一个课题来了。中国人不容易崩溃,道家来了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儒家往前进的,道家往后退的。退一步丢开很多世俗,看得更清楚。到了晚年,对人生的体悟更深,超越红尘了,这时候佛家来了,以前有名的文人,比如苏东坡、王维、汤显祖,也经过儒释道的三步的。
界面文化:那你会觉得年轻人读《红楼梦》或者苏轼、汤显祖是读不出来深意的,到了年纪增长才会有体会吗?
白先勇:我想这跟年纪的确有关系,我年轻时候看《红楼梦》,都是看林黛玉、贾宝玉、薛宝钗的三角恋爱,慢慢地(看到)背后有那么深刻的人生意义。我是劝同学们二十岁看一次、三十岁看一次、四十岁看一次、五十岁再看一次,完全不同的体验。有了心理准备,才能面对人生的挫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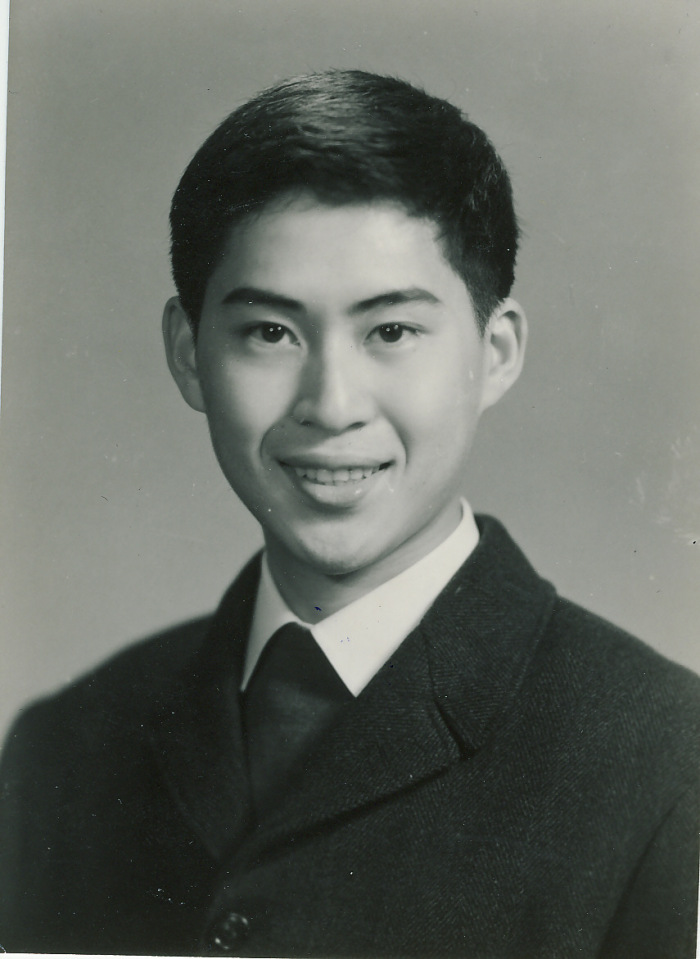
界面文化:那是有一点点悲哀,体验更加深刻是因为中年遭受了挫折。
白先勇:这是很多人的遭遇吧。我在美国教过二十九年的书,在台湾地区也教过书,人性差不多的,不管西方东方,人性几乎是普世的,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差不多。看懂了《红楼梦》对人世、人情世故都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文学教导我们如何同情,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,人们却常常忘掉恻隐之心。文学教我们如何对所有的人,不光跟自己的亲人,也包括其他人,怎么相处,怎么同情。有了同情,社会才不会有仇恨,仇恨是人类心中破坏性最大的力量。
界面文化:文学教育也包括对成功的教育吗?比如对追求功名利禄的反思?
白先勇:一个完整的人格比功利的成就在某方面说更重要。有的人不择手段变成一个富有的人或官位很高的人,还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呀。《红楼梦》宝玉出家,并不说是虚幻的逃避,而是对人生彻底了解后的做法。《红楼梦》并没有说偏向佛家,儒释道三家都是人生的途径,看你怎么选择。至于贾家的兴衰,这也是人生的现象,有兴必有衰,了解以后人生本来就是如此。
界面文化:从年少的时候提倡现代文学,到现在提倡中国传统文化,这当中有联系吗?
白先勇:是的,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西方文学,西方文学有伟大的成就。后来慢慢发现,自己的文化也有灿烂的成就,所以就制作《牡丹亭》,希望能带给大家新的认识。当初二十一世纪初制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时候,很多昆曲老师都退休了,昆曲界有青黄不接的危险,我们就训练一批青年演员,希望能把青年观众召回到戏院。那时候很多观众都昆曲无感,很疏离,《牡丹亭》就是歌颂青春、歌颂爱情的。二十年来演了五百多场,去过两岸四地,六十多个城市、四十多所高校。演员还是原版人马,二十多岁演到四十多岁,都到了最成熟的时候了。像我们的春香、演员沈国芳,很可爱,二十多年来形貌都没怎么变,还那么娇小玲珑。

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