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、王蒙70万字的巨著《这边风景》、李娟的散文新作《夜行车》……许许多多为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,足以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作品,都诞生于文学杂志《花城》。
文学是时间的证人,瞬间凝固成永恒。
今年,《花城》迎来45岁生日。8月17日,“万象向南——《花城》四十五周年暨第八届文学颁奖典礼”在广州举行,这也是2024年南国书香节的重要活动之一。李敬泽、麦家、陈晓明、阿来、东西、邓一光、蒋述卓、谢有顺等作家、评论家、文学编辑、出版人共同见证了这场文学盛典。现场还播放了一段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的散文影像,由原著作者李娟朗读。

《花城》45周年
一部小说,可以是一味药
第八届花城文学奖评选作品发表的时间范围为《花城》杂志2019年第1期至2023年第6期以及2020年至2021年3期长篇专号(5年,共33期杂志),设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奖等多个奖项。
其中,李宏伟的《灰衣简史》、张欣的《如风似璧》获得第八届花城文学奖“长篇小说奖”;丁颜的《雪山之恋》、尹学芸的《苹果树》、韩松落的《我父亲的奇想之屋》、杨知寒的《连环收缴》、阿乙的《二见未婚妻》获得“中篇小说奖”;班宇的《羽翅》、张楚的《和解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》、徐则臣的《宋骑鹅和他的女人》、焦典的《六脚马》、薛超伟的《化鹤》获得“短篇小说奖”;张执浩的《没有结尾的梦》、雷平阳《夜伐与虚构》获得“诗歌奖”;陈年喜的《人们叫我机师傅》、雍措的《越来越薄的等》获得“散文奖”;何平的“花城关注”系列点评获得“评论奖”。
在当代长篇中,《灰衣简史》是独特的一部。李宏伟说,《灰衣简史》延续亘古的追问,推想欲望、挣扎、救赎的母题如何在当下中国有效演绎。小说借用了药片与说明书的关系,以内篇、外篇为基本结构。“于我而言,这并非简单的对应或象征。今日世界,一部小说在实质上仍旧可以是一味药,至于是否有药效,是缓解还是治愈,则看作者与读者能否就服用的方式达成一致。”
张欣现场感谢了责编、评委、读者。她说,今天的文化活动非常多元,但读者依然拿出了宝贵时间来阅读。“读者的阅读,是我们创作的原动力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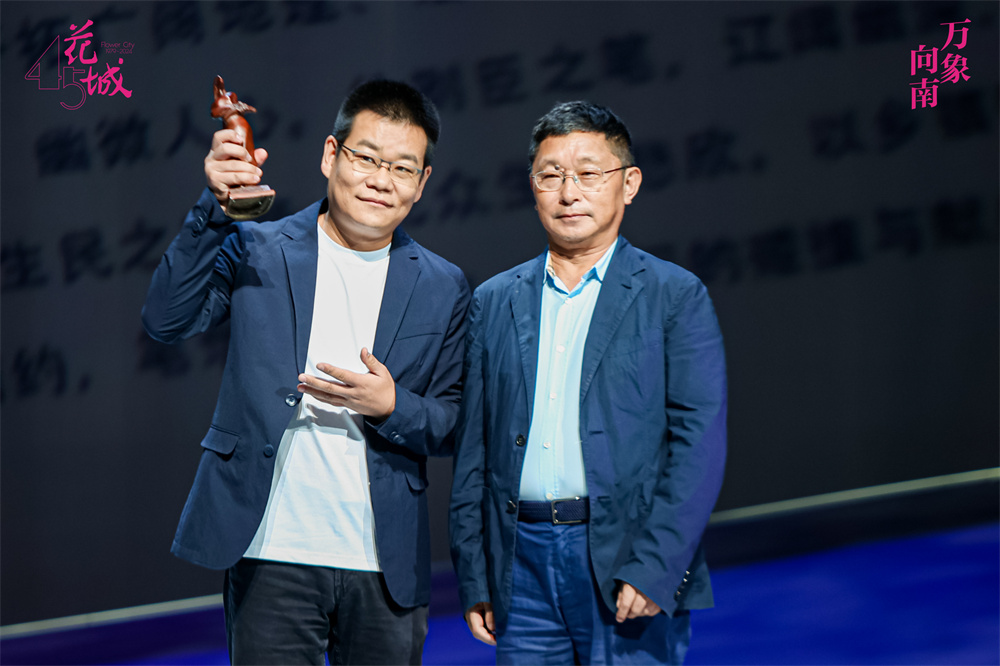
徐则臣和阿来
那些形形色色的灵魂
很多年里,徐则臣的写作都盯着水面看。水上有船,船上有人,船上的人生活单调乏味,千篇一律,简单的得就像没有生活一样。“我知道他们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,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,在两点一线的行程中,他们有着宽广、辽阔、翻江倒海但沉默着的内心戏。这些内心戏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。这些内心戏要表现出来,必须让他们下一下船。”
于是,《宋骑鹅和他的女人》就是宋骑鹅下船以后的生活真相。“写完这个小说,我疑心自己是不是下手太狠了。但似乎也只能如此:船上的生活有多平静,船下的生活就有多动荡;水上的生活有多简单,岸上的生活就有多复杂;船上的生活有多祥和,下了船就可能有多凄厉。所有在船上走稳了的人,上了岸都会脚步踉跄,仿佛大地真不牢靠。生活大抵如此。”
尹学芸的《苹果树》写的是有关乡村的传奇。文化、风俗、道德、传统、修为、信仰以及世道人心,在一座北方的村落展开的画卷。苹果树是一个媒介,不单系住了两家人的情感,也呈现了一座村庄的风情。“人物的命运,人心和人性的指向,在时代的变迁中呈现木本结构的纹理和年轮。木本结构不同于草本,有深根系统,可以多年生长。”
张楚的《和谢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》有关县城里形形色色的灵魂。“大多时候,他们的选择会和生活产生裂隙,在裂隙诞生与合拢的过程中,无法言说的痛苦、迷雾中的彷徨、身为人类的渺小感和对未来的憧憬如影随形。”张楚说,小说叙事的过程,其实就是小说家和人物、和自我、和观念达成和解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谈不上甜蜜,可仍让小说家乐此不疲。
韩松落直言《我父亲的奇想之屋》对自己非常重要,因为那是他在停止写小说很多年,再次回到小说世界之后的最早几篇作品之一。“我开始一次次走出我的屋子,叩开小说世界里那些隐藏的空间。我很喜欢这种叩击,也喜欢被眼前的壮美惊吓的感觉,此时此刻,愿我们都能在叩击中变得丰美,也愿我们叩开的壮阔世界,能够紧密相连。”
而对阿乙来说,《二见未婚妻》也有着特别的意义。2019年,他在“写作是为了作品好看,还是真实”之间选择了后者,《二见未婚妻》就是选择的结果。“它更多地体现了繁复而不是简洁,更多复活了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某个惊人的事件,它没有反转、反转、再反转,它只有比我们正常经过的时间要慢上几倍的时间。对我来说,这样的写作是革命和转向。”
写作的方法,生活的方法
让人眼前一亮的是,本届获奖者中,有五位85后、90后。
班宇说,《羽翅》现在看来是一个“来自过去的礼物”,小说本身写的也是对记忆中人的怀念和想象。在他看来,小说有时就是这样,它比我们说出的话语的存在时间要稍微长一点,也就在这么一点点额外的、多余的、礼物一般的时间里,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与故人们重逢。
焦典的《六脚马》是一个关于妈妈的故事。她坦言自己的母亲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好母亲,小时候她从不爱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,但多年后,在文学的世界里,她只深深回想起妈妈离家前一晚呼出的沉默的烟雾。于是在《六脚马》的结尾,她对着小说里的“妈妈”使力喊:“妈!你跑快点!”
《连环收缴》是杨知寒的第一个中篇,也和她的生活最贴近。“故事里的人渐渐逝去,故事也会消失。但故事里的情绪、情感、人性,会在以后的时空不断重现。我希望通过写作,保留记忆和一些珍贵的东西。”
薛超伟的《化鹤》写的是一个少年得病之后,身体受限,却拥有了更大的自由。“生活中总归有很多受限的时候,人常常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阻碍和困难,这时反而不着急了,停下来看看,这是怎么发生的,它究竟还会往什么方向发展。”薛超伟说,这是他生活的方法,也用在写作上,“我小说里那些看似很轻盈的部分,其实都是与障碍对抗之后幸存下来的。”
丁颜一直倾向于一种清净而自然的写作,但又因为年轻,写作时常常如同夜行在广袤的草原,难免有时会任意而为,失去方向,丧失信心。《花城》给了自己一份直面文学的勇气,也让她更加相信文学就是存在的被尊重,隐藏的被看见,逝去的被记住,当下的被展开,用生而为人的良心和责任给未来一份信息和希望。

五位年轻的获奖者。左起:班宇、丁颜、杨知寒、焦典、薛超伟
坚实生活,美好做梦
获得散文奖的陈年喜坦言自己非常感动和惶恐,因为他是一个民间的、边缘的写作者,一个老牌的“文学青年”。《人们叫我机师傅》描写的是一位矿山“开了一生机器的师傅”,他像一片树叶一般来到这个世界,又像一片树叶一样离开这个世界。“我想言说人和世界的关系,人活在这个世界的位置、方法和意义。”陈年喜说,文学关乎现实,也关乎梦想,他愿在余生里坚实地生活,美好地做梦。
雍措的《越来越薄的等》有关一个小村庄。越写这个小村庄,她越觉得自己写不完,越觉得它变得辽阔、广博。写着写着,她还发现自己和小村庄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——它不仅是生养自己的地方,也是自己的文学故乡。“我庆幸自己是一个有故乡的人。”
在张执浩看来,诗人的天职在于,用更精准的语言呈示我们繁复的内心世界,怯懦也罢,勇敢也好,报信人也罢,守夜人也好,诗歌最终要见证和抵达生命的意义。《没有结尾的梦》这组诗写于四年前那个非常特别的春天,“我相信,若干年后,当我们重新回溯那一段经历时,会重新获得一种宽阔而深邃的目力,并因此衷心赞美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。”
雷平阳说,一个诗歌的写作者写到满头白发的时候,看见一个个时代从自己身边喧嚣而过,深感寂寞、孤独。与此同时,笔下的诗歌也可能终将在时间中消失,而自己还得在原地不停地写下去,“一种不可置疑的腔调,一种从容不迫的展开方式,也许是自己抵抗寂寞与孤独,并往时间深处一直去寻找的存在。”

《随笔》《花城》
在爱与温暖的旅程中同行
值得一提的是,本届很多获奖作品首发于“花城关注”。自2017年第1期开栏,到2022年第6期结束,“花城关注”历时六年,计三十六期。而获得本届“评论奖”的,恰是何平的“花城关注”系列点评。
“今天中国文学有众多的期刊奖项。一组连续写作的系列点评能够获奖,也许并不多见。”何平感叹,因为“花城关注”,时任《花城》主编朱燕玲和从彼时到现在的“花城人”与自己成为同行者。“正是这些同行者,使得我一次微不足道的 ‘批评的返场’,一场自我命名的文学策展,成为爱与温暖的盛大文学旅程。”
1979年,《花城》《随笔》杂志创刊。《花城》杂志得名于秦牧先生的散文名篇,被誉为全国纯文学期刊的“四大名旦”之一,而《随笔》素有“南有《随笔》,北有《读书》”的美誉。1981年,花城出版社成立,八九十年代引领了钱锺书热、先锋文学热、 王小波热、武侠文学热、琼瑶热、席慕蓉热、朦胧诗热等中国出版和阅读潮流。
去年3月,花城文学院成立,通过签约名家、打造文学之夜、发布花城文学榜、启动创作项目、实现版权运营与孵化等多种形式。到了今年,“花城文学课”诞生,《我的阿勒泰》成为散文影视化现象级爆款作品,带动“李娟·花城”系列非虚构作品百万级畅销。
45年来,还有大量当代艺术美术作品作为插画展示在《花城》的纸页中。在典礼中,著名画家林墉作为艺术家代表,与女儿林蓝上台接受《花城》的致敬。
本次典礼由花城出版社、花城文学院、《花城》杂志与《随笔》杂志主办。在典礼引言中,主办方郑重地写下:花城四季繁盛,摇曳生姿。万象向南,沿途必有繁花灿烂,气象万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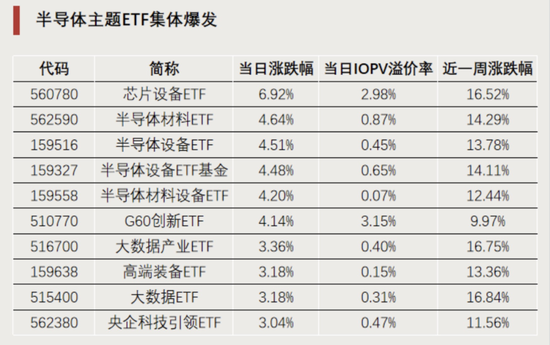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